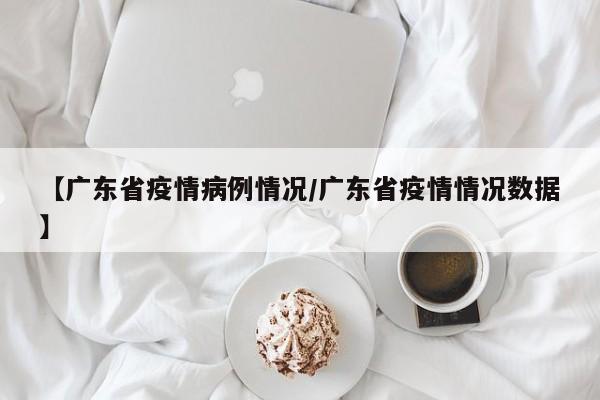在中国疫情防控的宏大叙事中,“武汉疫情”“上海疫情”等名称已被刻入公共记忆,但鲜少有人提及“郑州疫情叫什么名字”,郑州的疫情从未被官方或民间赋予一个特定名称,它更像是一段模糊而复杂的集体经历——没有标签,却深植于城市的肌理之中,这种“无名”状态恰恰折射出中国疫情管理的独特逻辑:淡化地域污名化,强调全国一盘棋的协同性,但也无形中掩盖了地方性创伤的个体表达。
郑州的疫情管理遵循着国家统一的“动态清零”政策,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多重压力叠加下的韧性应对,作为全国交通枢纽,郑州承载着超过1,200万人口流动的日常压力,京广铁路、郑西高铁和新郑国际机场使其成为疫情防控的“前线战场”,2021年7月暴雨灾害与疫情暴发交织,2022年富士康工厂聚集性感染引发员工徒步返乡事件,这些片段拼凑出郑州疫情的典型性——它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,更是城市治理、经济民生与人性考验的多维熔炉,官方通报中始终以“郑州疫情防控”或“河南疫情”代称,这种命名的缺席并非疏忽,而是有意避免地域标签带来的歧视或恐慌,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病毒学名而非地理名称一样。
但名称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记忆的空白,相反,郑州疫情的叙事是由无数个体声音编织而成的,社交媒体上,“郑州疫情”话题下充斥着市民的实时记录:志愿者在封控小区穿梭配送物资的画面、医护人员在高温中穿着防护服的疲惫身影、富士康员工徒步百公里回家的震撼视频……这些碎片化的表达构成了一个“去中心化”的记忆库,它拒绝被单一名称定义,却更真实地反映了城市的坚韧与挣扎,一名郑州博主在微博写道:“我们的疫情没有名字,但每扇窗后的等待都是历史的注脚。”这种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形成微妙互补——官方强调数据与政策成效,而民间聚焦情感与日常生存。
从更广的视角看,郑州疫情的“无名”状态是中国抗疫模式的一个缩影,国家层面,疫情被纳入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”框架,地域名称的弱化有助于强化集体主义精神,避免地方间相互指责或污名化,相比之下,国际社会常以地名命名疫情(如“西班牙流感”“德尔塔变异株”),但中国更倾向于用时间节点(如“武汉保卫战”)或抽象概念(如“动态清零”)来表述,这种差异背后是文化逻辑的深层分歧:西方强调个体与地方的标识性,而中国注重整体性与秩序稳定,郑州的例子证明,即便在没有名称的背景下,防控措施依然高度系统化——常态化核酸检测、健康码分级管理、物资保供链条的快速响应,均体现着技术治理的特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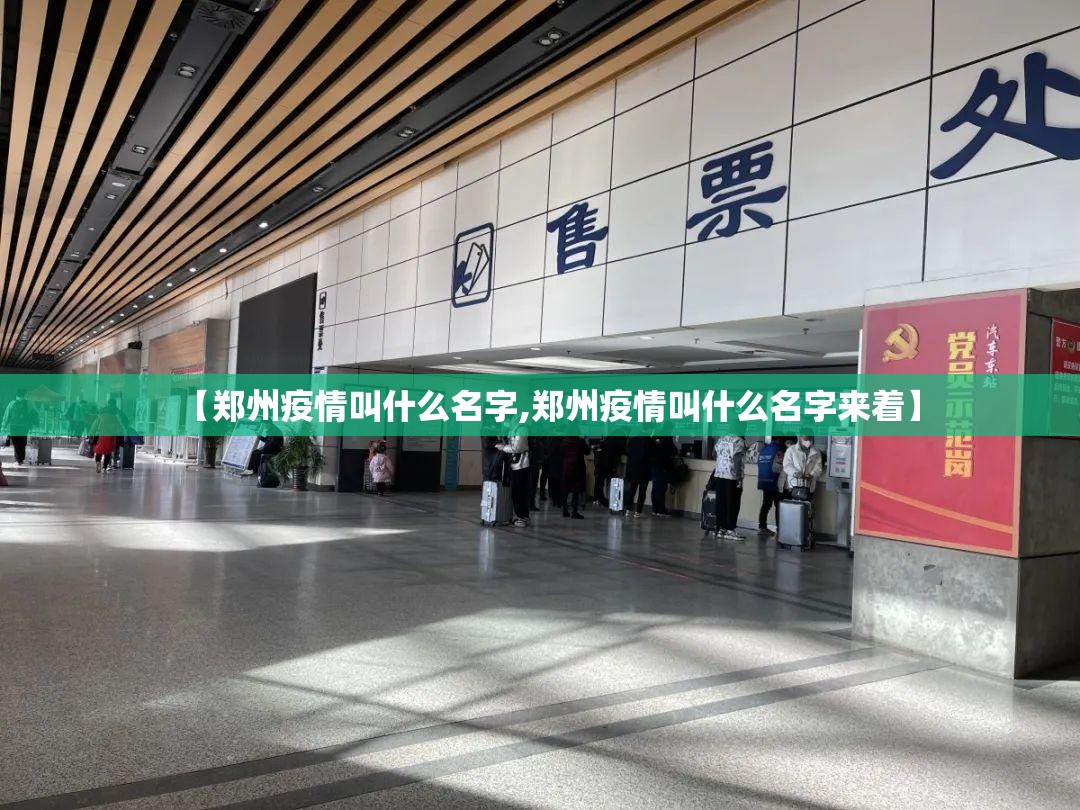
无名之痛也可能带来记忆的稀释,历史学者警示,缺乏具体名称的公共事件容易在宏观叙事中被简化,导致地方性经验被忽视,郑州疫情中,小微企业倒闭潮、农民工生计困境、学生网课长期化等问题曾引发广泛讨论,但这些细节未必能进入国家层级的集体记忆,正如德国学者阿莱达·阿斯曼所言:“命名是记忆的锚点。”郑州的“无名疫情”提醒我们,在标准化防控之外,仍需关注地方创伤的独特性。
郑州疫情或许不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,它的意义在于如何以沉默的姿态融入中国抗疫史诗——没有标签,却有温度;没有名称,却有痕迹,这座城市以它的方式证明:韧性不在于被铭记为何种符号,而在于普通人每一次有序排队核酸检测、每一句“加油郑州”的呐喊中,疫情终将褪去,但这份无名之下的集体勇气,或许才是最具生命力的历史遗产。
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