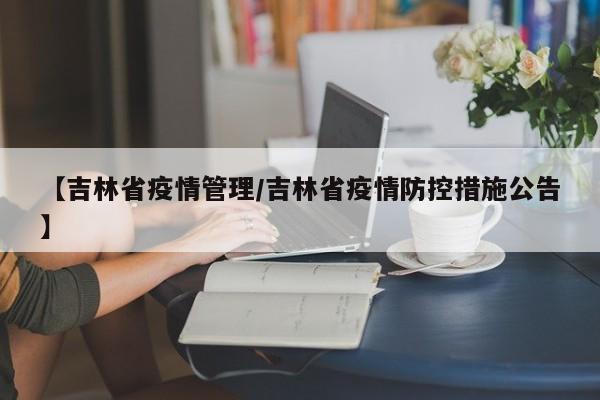2022年10月,郑州西郊某小区微信群突然弹出一条视频:一位老人颤巍巍地用粉笔在斑驳的墙面上划下第七道刻痕,这个隐秘的计时仪式,比任何官方通报更早预言了封城的延长——在健康码突然变红的那个午夜,在超市货架被抢购一空的凌晨,在铁皮围挡封死小区大门的拂晓,没有人能说清“郑州哪天封城”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封城从来不是日历上一个清晰的红色圆圈,而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生活突然断裂的叠加态,是权力与病毒共谋下的一场没有哨声的集体囚禁。
官方叙事热衷于制造精确的假象,2022年郑州市疫情防控第137场新闻发布会庄严宣告:“自11月25日零时起实施流动性管理”,这行优雅的官僚主义修辞,巧妙掩盖了此前富士康员工徒步百里逃亡时事实上的区域封锁,抹去了城中村提前七天已被铁板封门的集体记忆,当权者深谙“封城”二字在政治语言学中的敏感性,于是创造出一套迷宫般的替代词汇:静态管理、闭环管控、临时管控——每个术语都是一扇旋转门,让问责消失在语义的迷雾中,那些最终被计入“正式封城”的日子,不过是权力在完成事实管控后追盖的橡皮图章,如同先枪决犯人再签署死刑判决书般的荒诞程序正义。
而在民间记忆的维度,封城日期的表述呈现出量子态般的混沌,对金水区的基金经理而言,封城始于10月12日写字楼突然关闭的电梯;对中原区的菜贩来说,则是11月3日农贸市场被蓝色铁皮吞噬的瞬间;对数万富士康工人,封城更早发生在10月29日——当绝望的年轻人翻越厂区围墙,用双脚丈量回家之路时,无形的城早已落下闸门,这些分散的、私人的、带着创伤体温的记忆碎片,被算法平台的流量逻辑无情碾碎,当你在搜索引擎键入“郑州哪天封城”,得到的是经过SEO优化的标准答案,那些血肉模糊的个体时间线,早已沉没在404错误的数字坟场。
更令人窒息的是,我们正在主动将记忆权柄上交给数字寡头,社交媒体根据“用户兴趣”定制的信息茧房,让郑州某小区的封控比南极科考站更遥远;算法推荐机制不断强化“正能量叙事”,将个体苦难编辑成励志剧集的蒙太奇;甚至当我们试图用“郑州 封城 日期”这样的关键词拼凑真相时,搜索引擎早已布下“善意”的过滤网——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,被转化成了“郑州市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”的庆典通稿,数字集中营不需要带刺的铁丝网,只需让苦难无法被检索、被记忆、被讨论,就能实现完美的社会性清除。

在郑州某处尚未拆除的围挡缝隙中,仍可见到各种材质的计数标记:指甲划痕、粉笔数字、甚至用馒头屑粘成的圆点阵,这些原始的记忆装置,构成了对数字极权最悲壮的抵抗,当未来的历史学家试图考证这场旷日持久的囚禁,他们终将发现:真正的封城日期,刻在那些深夜抢菜用户的眼袋纹路里,藏在静默小区阳台合唱的回声中,写在透析患者辗转求医的路线图上,这些记忆或许永远无法被搜索引擎收录,但正是这些原子化的微观叙事,保存着时代真相最后的火种。
郑州的封城从未真正结束——它只是从物理空间的禁锢,进化成了更高级的数字形态,当我们习惯从APP推送获取世界真相,当我们的愤怒与悲伤被精准计算成留存率数据,当“哪天封城”这个问题需要向上亿条算法规则乞求答案时,每个人都已经住进了一座更宏伟的虚拟牢笼,而打破这座牢笼的钥匙,或许就藏在那位画粉笔痕的老人颤抖的手势中:在算法之外记忆,在许可之外言说,在遗忘之外存在。
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