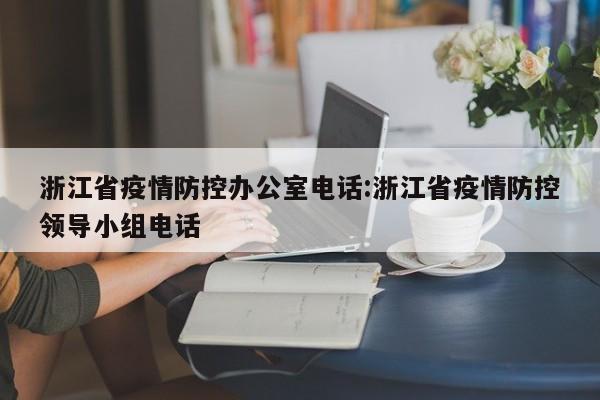初冬的郑州,街道比往常安静得多,金水区一条曾经熙攘的商业街上,“旺铺招租”的红纸在寒风中簌簌抖动,隔壁的玻璃门上贴着“疫情暂停营业”的告示,落款日期停留在半个月前,一家开业不到一年的奶茶店门口,店主小张正蹲在台阶上核对订单,身后是堆积如山的原料箱。“现在每天睁眼就是房租、员工工资、平台抽成,”他苦笑着指了指空荡的街道,“但至少我们还在挣扎。”
这不是某一家店铺的故事,自2020年以来,郑州经历了多轮疫情冲击,2022年秋冬的这波疫情更是让实体商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,据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,截至2022年11月,全市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较去年同期减少12.3%,餐饮、零售等服务行业闭店率高达18.7%,在这些冰冷数字背后,是一条条具体而微的生存战线。
“现金流就像悬在头顶的刀”
在大学路经营了八年豫菜馆的李老板,如今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盯着手机里的四个微信群。“堂食停了之后,我们把老顾客都拉进群,每天发菜单接龙。”他掀开后厨的帘子,指着正在打包的厨师苦笑道,“现在一份外卖赚三块钱,平台还要抽走两成,但不敢涨价——隔壁街两家餐馆上周涨价,第二天订单就掉了一半。”
更残酷的是固定支出的持续性压迫,一名二七区临街服装店店主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120平米的店铺月租2.8万,三名员工工资1.5万,加上水电物业每月净支出超过5万元。“现在日均销售额不到一千,账户里的钱最多撑到春节。”她摩挲着衣架上积灰的冬装喃喃道,“十年老店可能真要倒在这个冬天。”
裂缝中生长的生存智慧
绝境中,一些商铺正在裂变出惊人的适应性,中原万达广场的母婴店老板把直播间直接架在货架间,通过同城配送实现“云逛商场”;黄河路某书店推出“隔离阅读包”,读者盲选5本书由骑手无接触配送;更有火锅店将后厨改造成中央厨房,向周边社区供应半成品菜。
最令人动容的是民间自发的互助网络,纬五路上11家商铺组成“共生联盟”,餐饮店为隔壁花店引流消费满赠花束,美容院顾客可凭小票在咖啡馆享受折扣。“单打独斗肯定死,抱团还能喘口气。”联盟发起人赵女士说这话时,正忙着给暂停营业的健身房代收快递——她的美甲店成了临时驿站,反而带来了新客源。
政策救援与人性微光
政府部门并非没有行动,郑州市10月出台的“助企纾困十条”明确提出减免国有房产租金、发放消费券等措施,但不少个体经营者反映,政策落地存在“玻璃门”:某文创园区虽然公示减免三个月租金,却要求商户先全额缴纳再排队申请退费;某区承诺的纾困贷款需要提供房产抵押,让大多数租铺经营者望而却步。
真正支撑店铺活下去的,往往是市井生活中生长出的柔软力量,管城区某小区菜店老板坚持每天给独居老人留出特价菜,解封后老人们带着全家来购物;面包店每天打烊前把未售完品挂上“待用面包”树形架,需要者自行取用反而带动了日销增长,这些微光聚成的暖意,比任何商业教科书都更深刻地诠释着“社区经济”的本质。
后疫情时代的商业觉醒
当问及疫情结束后的打算时,大学路餐馆李老板的答案出乎意料:“就算恢复堂食,我也会继续做社群运营,这次逼着我们真正触达了顾客。”他打开手机展示着500人的微信群,里面不仅有菜单接龙,还有顾客自发分享的烹饪视频——某种程度而言,疫情强行完成了传统商铺的数字化启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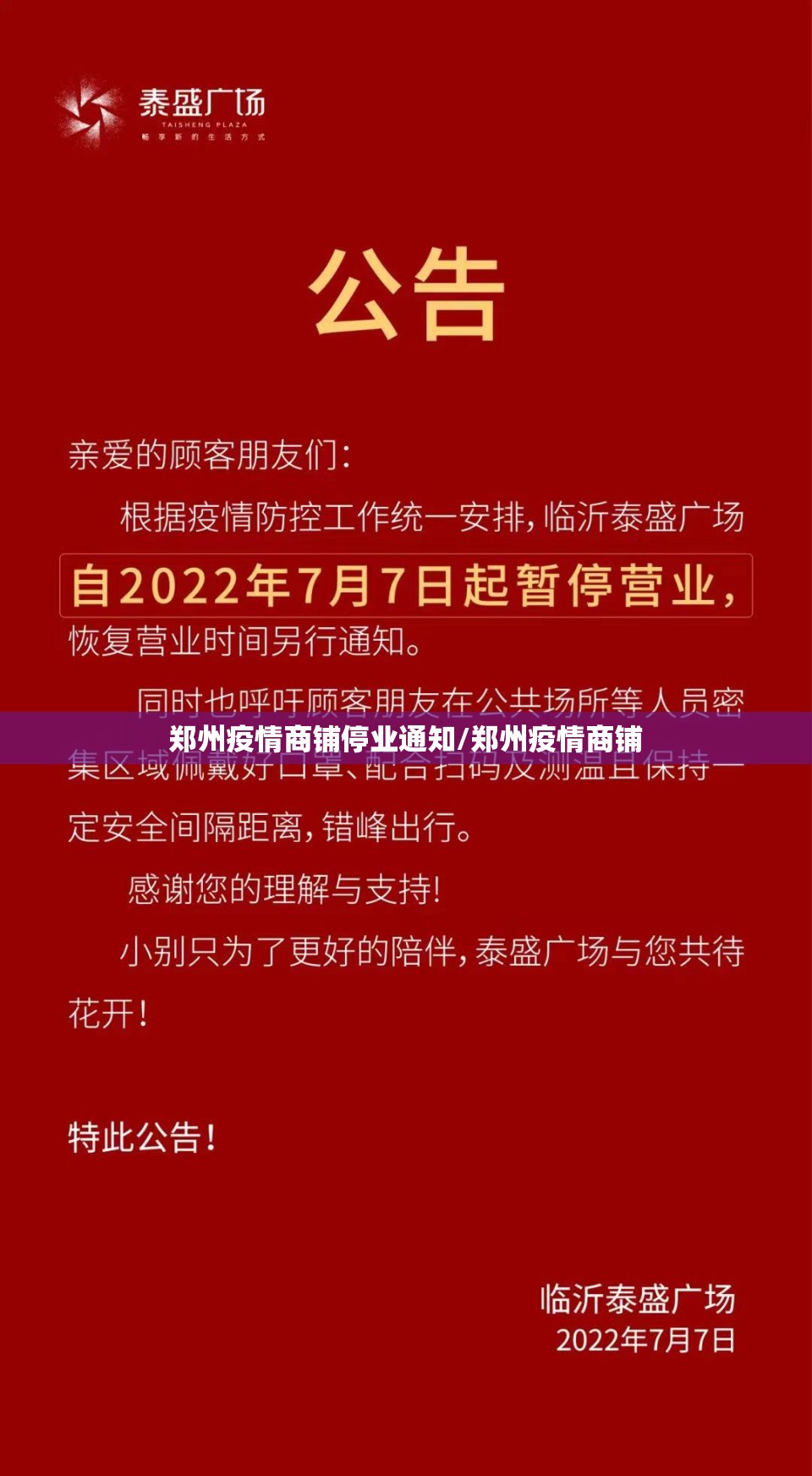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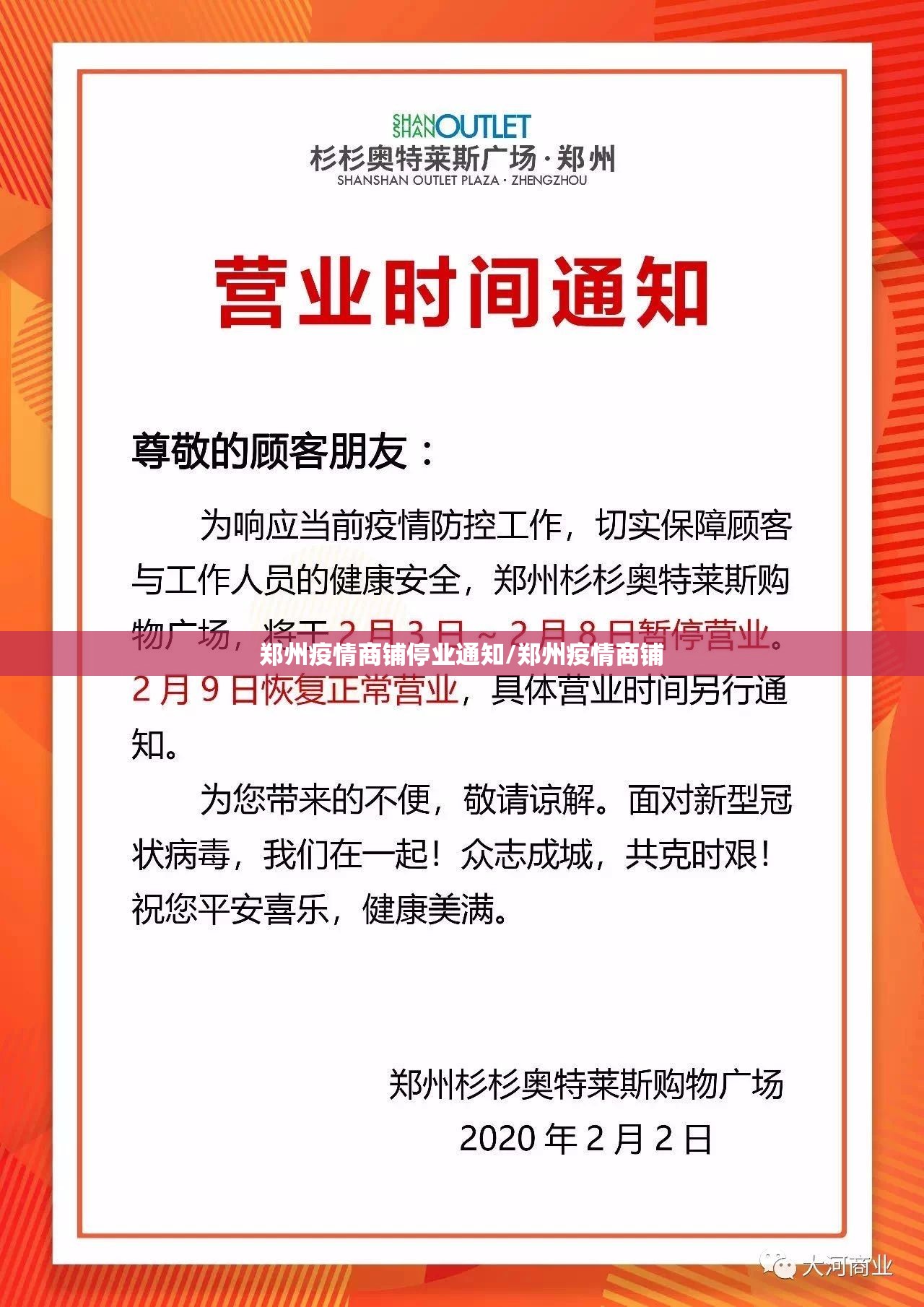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琦指出:“疫情像一场残酷的压力测试,暴露出单一经营模式的脆弱性,survivable(能存活)的商铺必然是线上线下融合、深度嵌入社区网络的节点。”
暮色中的郑州华灯初上,空旷的街道上飘着胡辣汤的香气,某家亮着灯的店铺里,打印机正吐出新的外卖订单,暖黄色灯光透过防疫塑料帘,在水泥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,这些光点或许微弱,但从未熄灭——就像这座城市商业脉搏的心电图,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,记录着最低谷的曲线,也预示着下一次心跳的来临。
(注:文中数据及案例基于公开报道整合,人物姓名为化名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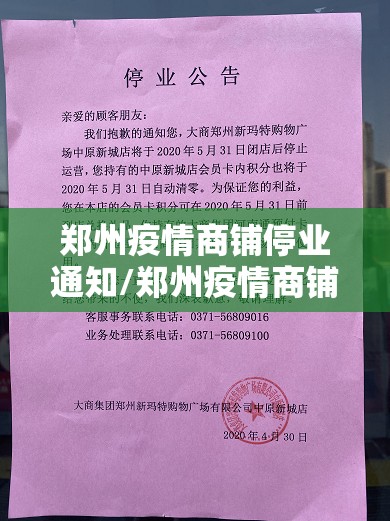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