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年初春,长春宽城区的一条街道上,风吹过空荡的公交站台,只剩下红绿灯在寂静中规律地切换颜色,这是一个平常的北方城区突然被疫情按下暂停键的时刻——而在这静止的表象之下,一场无声的战役正在激烈进行。
3月7日,宽城区报告本轮疫情首例本土确诊病例,七十二小时内,病毒隐秘的传播链已延伸至超市、小学、公交线路和老年活动站,区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,将防控区域划分为封控区、管控区和防范区三级网格,如同一位外科医生精准下刀,试图以最小代价阻断传播。

“我们不是在和病毒赛跑,而是在和人性博弈。”宽城区疾控中心主任王磊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样说,他的团队在最初96小时里只休息了不到十小时,流调队员穿梭在老旧小区与现代化商圈之间,背后是宽城区独特的城乡结合部格局:这里既有九十年代的老式职工宿舍,也有新开发的高层住宅小区,人口结构复杂,流动率高,给精准防控带来巨大挑战。
而在静默的城市表面之下,生活的脉搏并未停止,在凯旋路某封控小区,志愿者小李每天穿着防护服上下楼梯超过百次,他记得一位独居老人不会用手机订菜,每天在窗口用粉笔写下自己需要的食材:豆腐、白菜、两颗西红柿。“我们不只是送菜员,还是临时子女。”他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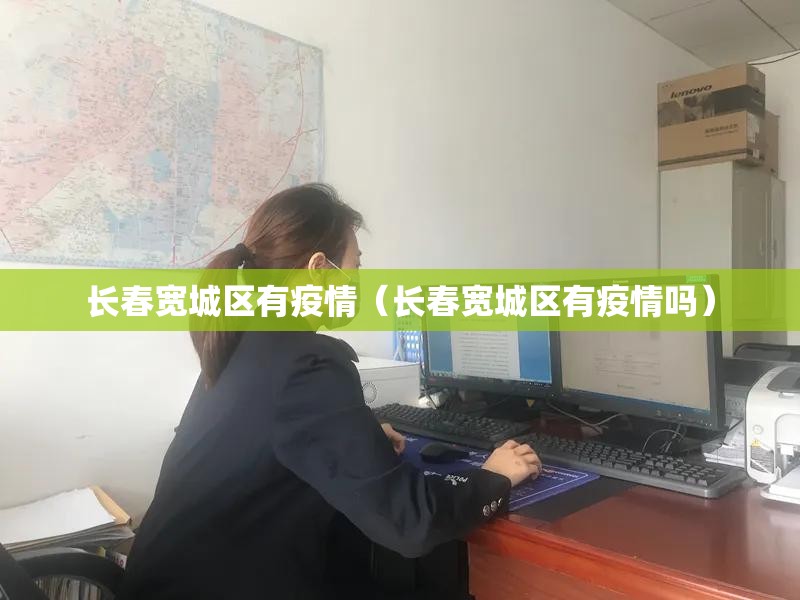
宽城区的疫情也成为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压力测试,线上,全区57个社区建立了“网格群-楼栋群-单元群”三级信息传递结构;线下,社区工作者和下沉党员组成“配送小分队”,保证物资最后一百米的畅通,新兴的社区团购模式与传统的居委会台账管理结合,形成特殊时期的“数字+人情”双轨制服务模式。
这波疫情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宽城区的核酸检测策略,基于人口密度和年龄分布特征,检测点被科学设置在学校的操场、停车厂和公园开阔处,针对老年人多的区域,检测时间提前至早晨七点;而在年轻租户集中的公寓区,则设置夜间检测通道至晚上十点,这种精细化操作使得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完成时间从最初的26小时压缩到最后的14小时。
到3月17日,宽城区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,十个日夜中,这个拥有80万人口的城区用近乎苛刻的精准防控,避免了全面封城的代价,当孩子们重新走在上学路上,当早餐铺的蒸汽再次升起,那些防护服下的压痕、志愿者手上的冻疮、社区干部沙哑的嗓音,都成为了这段特殊时期的注脚。
宽城区的疫情应对启示我们:现代城市的抗疫不仅需要科学手段,更需要人文温度;不仅要追求效率,还要注重精细;不仅要依靠技术,更要依靠社区纽带,当疫情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页,这些在危机中凝聚的智慧与温情,或许将永远改变这座城区的肌理与记忆。
寂静终会退去,而宽城区的春天,正在解冻的土壤下悄然萌发新芽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