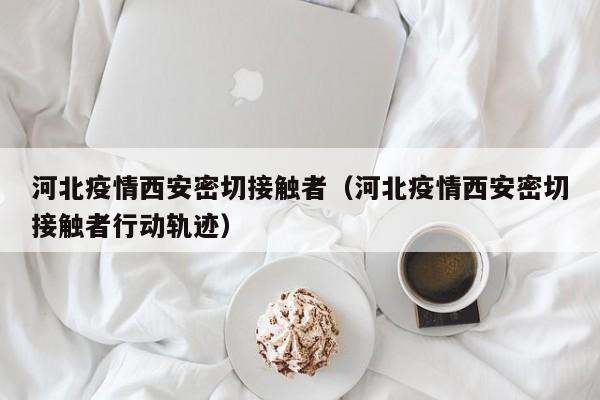在郑州师范学院行政楼的第三层,教育处的门牌安静地悬挂,这扇门背后,是一整套精密运转的官僚机器——培养方案审定、学籍管理、考试组织、成绩录入,表面看,这里只是高校里一个平凡的中枢职能部门;深入审视,它却是中国高等教育肌体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微观标本,一个被无形规则彻底驯化的“平庸帝国”,流程的正当性永远碾压教育的本质,权力的安全逻辑永恒扼杀着创新的冲动,这不是一个部门的沉沦,这是一整套体制文化的病理切片。
教育处的日常,实则是文件与印章的“仪式性舞蹈”,每一份教学计划变更申请,必须在三个科室流转八道签字;每一场期末考试安排,需经历五轮会议研讨方能最终定稿,这些流程被冠以“严谨科学”之名,实则早已异化为自我重复的闭环仪式,处长们关心的并非“这项改革是否真能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”,而是“这份批复是否符合上一级红头文件的最新表述”;科员们钻研的不是“如何优化实习流程提升学生实践能力”,而是“如何将材料装订得更为整齐以应对评估检查”,规则,这本应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,已然异化为目的本身,人的能动性、教育的创造性,在这套自我繁殖的流程正义面前,沦为微不足道的祭品。
这种“规则崇拜”的背后,蛰伏着根深蒂固的“避责”哲学,在一个问责压力无处不在的体系中,不作为的代价远小于创新失败的风险,教育处最聪明的生存智慧,便是“不做不错,少做少错”,任何带有不确定性的教学改革方案,最安全的归宿便是“退回修改”或“无限期搁置”,一位年轻教师充满激情地提交跨学科课程计划,历经半年磋商,最终被一句“暂无先例,需谨慎论证”轻松扼杀,这种规避风险的集体无意识,像低温一样缓慢凝固了整个部门的生命力,将教育处改造为一间遵循官僚熵增定律的“无菌室”——绝对安全,绝对正确,也绝对虚无,人性的温度与教育的热忱,早在文件传递的冰冷轨迹中消散殆尽。


更令人窒息的是,教育处的运作逻辑完美契合了马尔库塞所批判的“单向度”社会模型,它高效地消解一切异质思想,将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、可盖章的流程、可汇报的数据,学生不再是渴望被点燃的智慧火种,而是需要被妥善管理的学号编码;教师不再是启迪心智的灵魂工程师,而是必须服从教学日历的生产单位,这套系统通过“无害化”处理所有非常规诉求,成功生产出思维和行为高度同质化的“教育官僚”,他们精通所有规则语法,却唯独丧失了教育的灵魂叩问能力——而这,恰是行政化大学管理机构最为深刻的异化:在繁琐事务中溺毙终极意义。
指责教育处里的个体是廉价的批判,他们非天生官僚,而是被镶嵌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行动者,他们的理性选择,恰恰是系统所激励和嘉奖的,要撼动这座“平庸帝国”,不能寄望于道德说教,必须重塑其深层激励结构,或许可以引入校外专业力量对行政流程进行效能评估,将“师生满意度”而非“文件完备度”作为核心考核KPI;或许应建立跨学科的课程改革委员会,让一线教师与学生代表拥有实质性否决权;又或许需探索“行政休假”制度,让教育处职员定期回归课堂,重燃其对教育本真的感知力。
郑州师范学院教育处的故事,是中国高校行政化的一个精准缩影,它警示我们,当教育的灵性被官僚程序的繁文缛节所捆绑,当创造的火花被规避风险的保守哲学所浇灭,大学终将退化为发放学历文凭的标准化工厂,这座“平庸帝国”的围墙,并非由砖石砌成,而是由恐惧、惰性与僵化的规则构筑,它的倒塌,不需要壮烈的轰鸣,只需要每一个教育参与者对无意义流程的自觉拒绝,以及对恢复大学本真精神的执着信念,唯有如此,行政的齿轮才能重新啮合教育的初心,我们才能期待在未来的某天,教育处那扇门的背后,滋生的不再是规则的荒芜,而是思想的蓬勃春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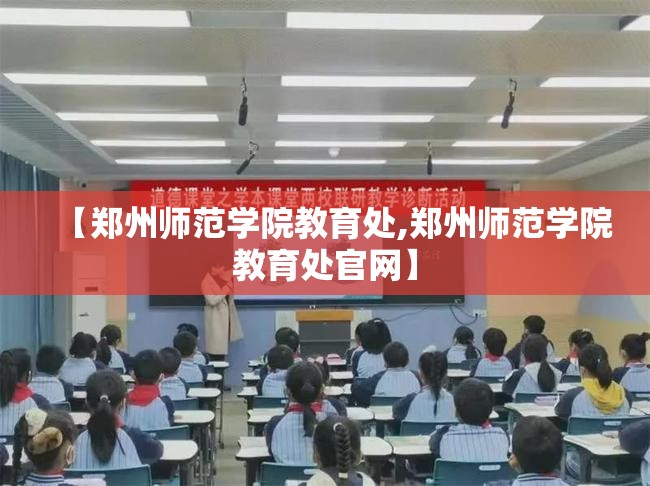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