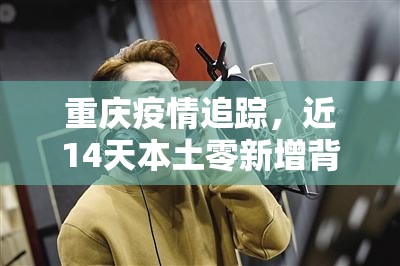雾气笼罩的渝中半岛,霓虹依旧闪烁,却照不见往日的车水马龙,2022年夏末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重庆拖入寂静——商场歇业、轻轨减班、洪崖洞空无一人,但在这座以火辣闻名的城市里,一种更深沉的情绪在暗涌:不是恐惧,而是“疚”,一种交织着自责、无奈与坚韧的复杂情感,正成为重庆人共同的心理底色。
“疚”从何来?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防疫叙事,重庆的愧疚感源于其独特的城市基因,作为中国最大的直辖市,重庆有着3000万常住人口,其中外出务工人员超过800万,疫情暴发后,许多在异地打拼的重庆人因“渝康码”变黄被迫滞留他乡,社交媒体上#对不起重庆#的话题下,满是游子们的道歉:“是我给家乡添乱了”,这种将公共危机个人化的倾向,折射出巴文化中强烈的集体主义烙印——正如三峡移民时那句“舍小家为大家”,重庆人总习惯将责任扛在自己肩上。
火锅店老板的深夜独白 在江北经营十年老火锅店的陈建国,第三次贴出“暂停营业”通知时,第一次在员工面前红了眼眶。“最对不起跟了我八年的炒料师傅,他说这辈子就没见过鸳鸯锅卖不出去的时候。”但愧疚很快转化为行动:他主动将库存的200斤牛油底料分装成500份,通过社区志愿者送给隔离中的老街坊。“火锅是重庆人的胆,不能让人心凉了。”这种从“疚”到“行”的转变,恰似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——愧疚的浊流与行动的清波碰撞后,反而奔涌出更强大的力量。
网格员的“错位愧疚” 二十七岁的社区网格员李娟,每天接听300通防疫咨询电话后,总会对着两岁儿子的照片发呆,因为负责高风险楼栋排查,她连续三周住在居委会折叠床上,视频里儿子哭喊着“妈妈不要病毒”时,她第一次对职业产生怀疑:“我保护了陌生人,却亏欠了最该保护的人。”这种防疫工作者特有的“错位愧疚”,在重庆并非个例,南岸区卫健委数据显示,疫情期间约43%的一线人员出现焦虑性自责症状,但正是这些自觉“不够好”的普通人,筑起了感染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值的防疫长城。


藏在辣椒里的哲学 有趣的是,重庆人化解愧疚的方式极具地域特色,心理学教授张渝生发现,当地居民在隔离期购买最多的非必需品是火锅底料和辣椒酱:“辣味带来的痛觉刺激,恰好对冲了愧疚引发的心理不适。”这种“以痛治痛”的应对机制,暗合了重庆人骨子里的生存智慧——就像山城陡峭的梯坎,越是难行越要昂着头走,当其他城市用“加油”互相鼓励时,重庆人更爱说“莫慌”,短短两字既是对他人的宽慰,更是与自己的和解。
从愧疚到共生的转型 如今回望那段特殊时期,会发现“重庆疚情”早已超越疫情本身,当无人机拍下志愿者骑着摩托车在盘山路上运送物资的灯光长龙,当“00后”女孩用剪纸记录核酸筛查点的日与夜,愧疚已蜕变为更深刻的城市共同体意识,这种情感进化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珍贵样本——它证明危机应对不仅需要科学防控,更需要情感维度的修复与升华。
夜幕下的长江索道再次穿行时,车厢里仍贴着隔座就坐的提示语,但重庆人已学会与愧疚共生:它不再是沉重的负担,而是映在江面的灯火,照见脆弱,更照亮前路,这份深植于巴渝大地的“疚”,最终长出了比黄桷树根更坚韧的力量——因为真正强大的城市,从不敢忘却疼痛,却永远在疼痛中向上生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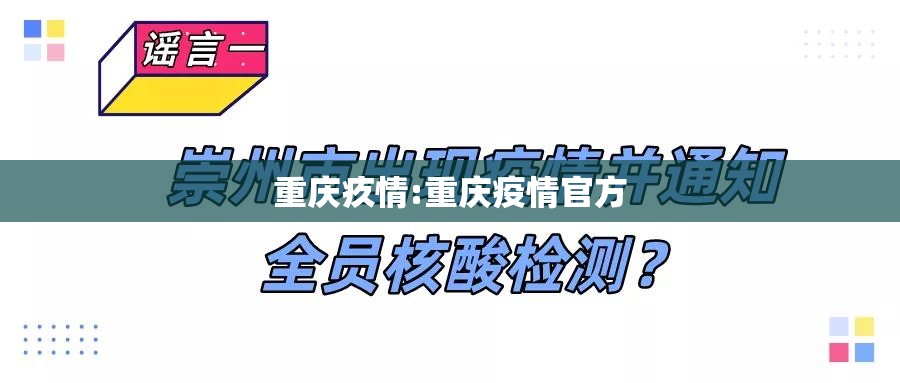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